
黃昏時分的衡水湖上,船夫搖櫓返回岸邊。
春日里,我來到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區,沿著衡水湖畔的中湖大道徐徐而行。微風吹皺清澈的湖水,一道道波紋隨風起舞,春的色彩與生機也隨波紋蕩漾開去。
湖水中爭先報春的是候鳥天鵝,它們雖然只在這里歇歇腳,嬉戲一番,卻總能給人帶來驚喜。花中的“報春使者”則是迎春花,在枝條交錯的樹叢中,迎春花嫩黃色的花朵雖小,卻非常醒目,似乎專為傳遞春天的訊息而來。冬青雖然在冬天也是綠的,但一場春雨后,冬青新葉顯露出只在春天才有的嬌嫩綠色。柳樹的枝頭仿佛被巨大的板刷抹上朦朧的綠色,遠遠望去,一派生機盎然,走到樹下,才看到枝條還未完全褪去冬裝。
春和景明,我去尋訪古城冀州的舊跡。在衡水湖邊不遠處,有一處冀州古城遺址,默默見證著這片土地上的世事變遷。當年大禹治水,劃天下為九州,冀州為九州之首。盡管上古冀州是一個地域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的冀州,但現今的冀州源自兩千多年前的信都城,仍然屬于上古冀州的地域范圍內。

冀州古城遺址。
冀州古城始建于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漢、唐時期的夯土城墻,在北宋時期為防御外敵,得以擴建。到明清兩朝,城墻經過多次修繕,并改為磚砌。值得慶幸的是,冀州古城東北面的一段城墻被保留至今。歷經2000多年的風雨沖刷,古城墻高低起伏,斷斷續續,某些地段似墻,某些地段像墩。
在冀州古城的遺址上,許多樹根盤根錯節地依附在墻體上。凝神望去,恰恰是這種歲月帶來的滄桑,讓人仿佛置身于歷史興替當中,不禁浮想聯翩。公元309年,后趙開國皇帝石勒攻克信都,曾在這里指點江山;公元531年,權臣高歡曾在此起兵,次年便攻入洛陽,擁立北魏孝文帝之孫元修登基;公元756年,唐代叛臣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令叛軍首領史思明經略河北,史思明行軍至信都城下,迫使信都太守烏承恩投降……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冀州城頭吟詩道:“昔人城邑中,今變為丘墟。昔人墓田中,今化為里閭。”冀州古城雖多次因戰亂遭到毀壞,但在勤勞的冀州人手中一次次煥發生機。
與冀州古城墻相互輝映的是古護城河。城墻上刻滿了歲月的痕跡,護城河則水平如鏡,不見白云蒼狗。河中一半是水面,一半是蘆葦。季節未到,蘆葦尚且枯黃。蒼鷺、骨頂雞、斑嘴鴨等鳥兒就在這蘆葦叢中安家,躲過了上一個冬天的勁風。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冀州古城的前世今生,衡水市在這里建起了古城遺址文化公園。從“九州開序”到“晨風伊始”,從“大漢星河”到“河朔名都”,從“陸澤裊升”到“明清故往”,行走在公園里如同穿行歷史長河,真有些一眼千年的恍惚之感。
我走走停停,從冀州古城遺址又回到了衡水湖邊。走進濱湖公園,紫荊、連翹、榆葉梅、藍亞麻、大濱菊等花卉已悄然綻放,漸成爭奇斗艷之勢。春天的湖水像一面鏡子,映出藍天白云,也映出湖邊每一個人的影子。湖水雖然不會攝影,但它能把每一個走過湖邊的人收藏在歷史的記憶中。早在漢魏時期,衡水湖就已聞名四方,曾被稱為博廣池。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曾在《水經注》中稱博廣池“多美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我想,酈道元在出任冀州長史時,或許也曾對著這煙波浩渺的湖面出神,漫步在朝霞初照的清晨和夕陽入湖的黃昏。
離開濱湖公園,我來到老鹽河生態公園。老鹽河是河北平原上一條古老的河道。北宋時期,黃河在河南省濮陽市西部的小吳埽決口,向北沖出三條新河道,其中一條便是老鹽河。滾滾黃河水沿著老鹽河等河道向北流去,直至北宋滅亡后,南宋高宗為了阻止金兵南侵,在河南省滑縣境內扒開黃河南堤,迫使黃河向東流入黃海,黃河離開冀州。后來,其他河道被不同的江河占領,唯有老鹽河,因為河床地勢高,其他河水難以流入,作為黃河故道被保留下來。
作為冀州的歷史遺存,老鹽河經過流域改造與生態修復,在保留原有地貌、古樹、水系等自然風貌的基礎上,建起了一座集鳥類保護、濕地觀光、生態園林于一體的公園。千年古河道窄處像河,寬處若湖,沿岸銀杏、黑松等喬木和紫丁香等灌木高低錯落,親水平臺和生態棧橋則延伸至水中。站在岸邊舉目望去,雖然不見當年黃河的奔騰與咆哮,但可以任由思緒回到過去,古城冀州的風云變幻依舊讓人心潮澎湃。
漫步著,漫步著,我既陶醉于這被碧水環繞的冀州春色,又沉思于花紅柳綠掩映著的厚重歷史……
攝影 陳康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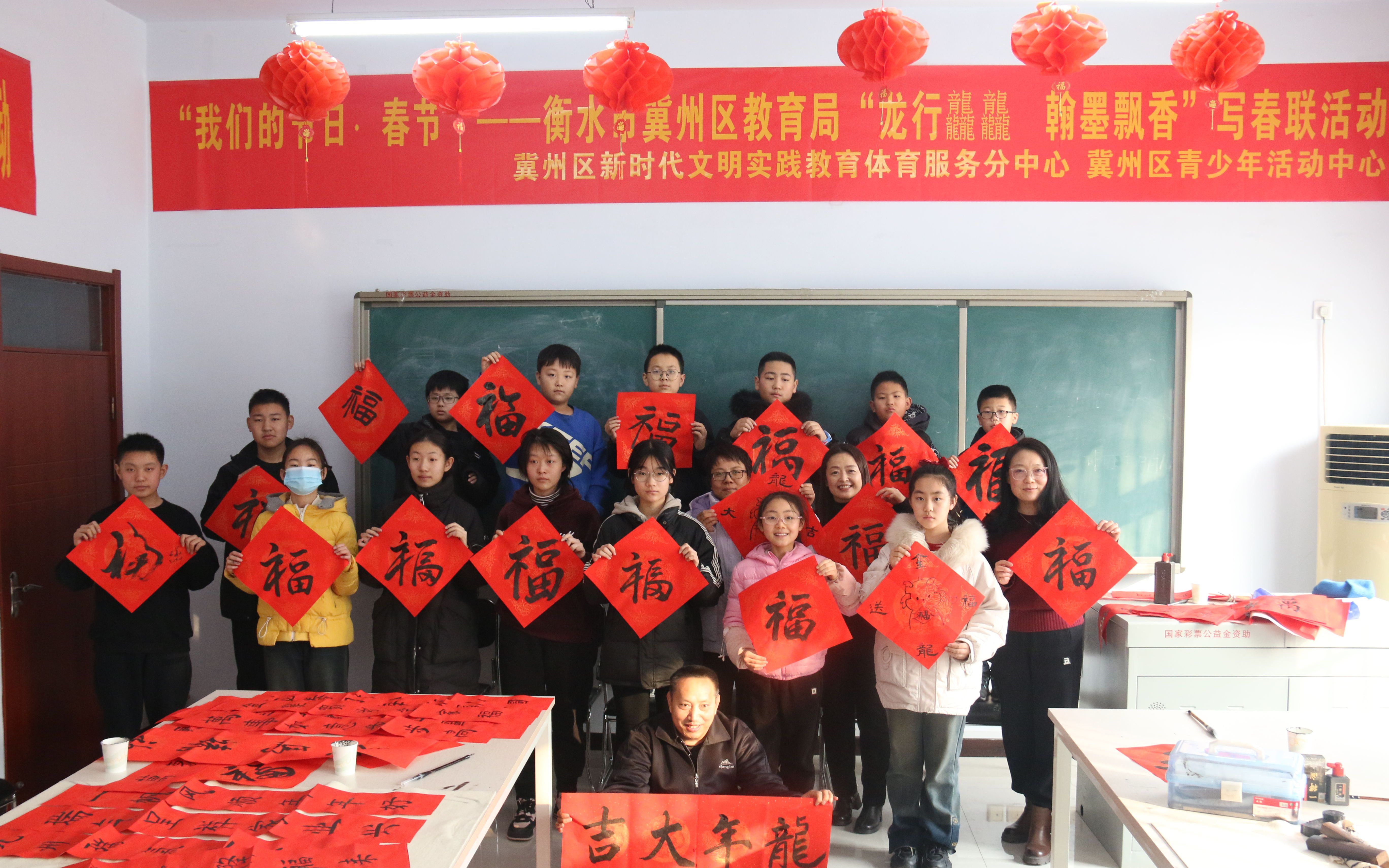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