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對于現代中國人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人口流動的歷史。革命、戰爭、饑荒和瘟疫,都曾讓幾代中國人遠離故土,成為不同意義的“異鄉人”。那時候的流離失所,多少帶著一些悲壯和無奈。
中國急速的改革,更是加速了流動進程。經濟的發展和政策性的鼓勵,讓人口的流動前所未有的巨大,“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不再具有現實的召喚意義,人們被新的時代精神感召,求學或打工,下海或漂泊。在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有的人迎頭趕上,有的人則被狠狠甩下。
故園的凋敝催生了城市的興起,城市化的進程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必然改變了中國人的家庭結構。但在靈魂深處,中國人的家國觀念依然在每年的春運到達頂峰。只是,“過年回家”這個簡單的詞組,被不同的人賦予了不同的含義。
電影,是表現事態人心變遷的有效載體。在關于人口遷徙和流動的電影中,有著一條不甚清晰但隱隱存在的關于中國人流動和變遷的歷史脈絡;而這種變遷所體現的,正是當代中國人面貌和精神的變化。
瓦解的家庭:轉型時代的陣痛
19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中國人的故土觀念開始松動,南北發展不平衡,城鄉差異加劇了人口流動,一種非政策性的自覺的移民潮開始涌現。由此,傳統的家庭結構,也漸漸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新的經濟形勢和舊有的家庭觀念,必然發生沖突。
1991年黃健中導演的《過年》,就直接表現了變革時期舊有家庭倫理的消逝。電影以大年初一這一天東北農村老程家五兄妹等人的矛盾為故事核心,展現了新和舊的沖突。
老父親在外打工辛苦了一年掙了不少錢,本想回家過個好年,年三十這天卻沒有一個孩子回來,只能和老伴相伴。大年初一,孩子們終于一個個回了家,每個人卻各懷心思。洞穿了這一切的老父親,為大家端上了最后一道大菜:一沓沓人民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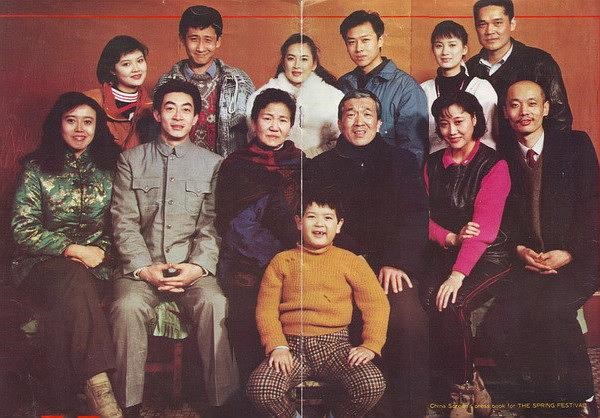
黃健中《過年》的海報。
這部電影為我們展開了一組改革開放后的世態人心群像:長子木訥老實,大媳婦世俗刁蠻,唯利是圖;大姐夫拈花惹草,大女兒隱忍委屈;二兒子在外讀書找了高干女兒做女友;小兒子卻不務正業,貪圖享樂;二女兒則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靠努力發家致富的個體戶……
在這部電影中,處處出現新舊時代的對比:傳統大家庭的父權制和現代三口之家由經濟實力決定家庭地位,體制內鐵飯碗的瓦解和個體暴發戶的一擲千金,代表前現代的馬車被現代文明的產物小汽車替代等,無不展現出在時代轉型期的家庭劇變帶給人們的撕扯感。
事實上,這一家人不論發心如何,很難說誰是真正意義上的壞人,但其表現的困境,確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新的經濟制度必然帶來新的家庭結構,但人心和倫理卻不會那么快轉變。在矛盾之中,必然就存在一種戲劇性的張力。這種張力普遍存在于中國人的家庭之中,過年聚會的形式讓矛盾集中爆發。電影的結尾,傷心的老兩口,拋下了一大家子人坐上了馬車駛向了遠方。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第五代”導演夏鋼拍攝的《大撒把》,巧妙地把握住新生的都市中產家庭觀念的變化,有機會的人們對國外的向往強烈到可以放棄家庭責任。片中男女主角的伴侶,都因為種種原因出國在外,留下他們獨自在國內。
電影很多橋段都處理得頗具喜劇感,因為怕趕不上去加拿大的飛機,丈夫把自己懷孕暈倒的妻子(女主人公)緊急托付給一位陌生男子(男主人公),興奮地飛往異國。男主的妻子也因為要出國,拋下了他一人留守。
偶然的機會,兩個受傷的人重逢,一起過年,組成了“臨時家庭”,摩擦出了情愫,但又不得不面臨女主即將遠赴加拿大的現實。電影用男主人公的對話,表達了主創對“出國潮”的看法:“我知道,你這一走就是肉包子打洋狗了......”“外國領事要是再給你拒簽,你就拿外語教訓他們:當年你們的爺爺奶奶們跟著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時候,誰跟他們要過簽證?!”
凡此種種今天看來頗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對話,折射出的是當年的輿情,去還是留?這個問題,就像電影里男女之間情感的道德危機一樣為難。在電影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機場分別,電影就此戛然而止,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局,也留下了一個曖昧的判斷。
家國同構:以家庭作為隱喻
1999年的世紀之交,各種時代病癥似乎到達了文藝表現意義上的高峰。“第六代”導演張元拍攝了《過年回家》,以一個女犯人的過年回家之旅為主要故事線索,以家庭困境隱喻時代困境,將個人的遭遇與時代問題同構。
主人公陶蘭因為不滿繼父的女兒小琴誣陷自己偷了五元錢而失手將其打死,釀成了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劇。十七年后,服刑期間的優秀表現,讓她獲得可以過年回家的機會。在女警的陪伴下,陶蘭的回鄉之路變得格外特別。常人團圓的喜悅,對于陶蘭來說是矛盾的,“近鄉情怯”不是一句文藝的表達,而是一種切實的體會。到家后,她還是求得了父母的諒解,卻跪在地上承認了五塊錢是自己偷的。這句話,也許是為了安慰繼父的喪女心痛,卻以侮辱自己為前提。與其說,這是一部講述親情回歸的作品;不如講,它表現了時代對人的異化。
同為“第六代”,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把握到了流動和變遷現實中的魔幻。電影用男女主人公各自尋找伴侶的故事,深化了導演一如既往的關注:外部世界的劇變,讓人的情感和內在破碎。

《三峽好人》劇照。
煤礦工人韓三明和女護士沈紅從山西來到重慶奉節,分別尋找到了自己已離開十六年的前妻和分別兩年的丈夫。兩個來路不同的異鄉男女在奉節擦身而過,苦尋之后,他們還是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電影畫面無數次略過三峽的江景,盡管片中人無心欣賞,但鏡頭記錄了一段歷史。在他們身后,是突然飛升消失巨大建筑物,用一種超現實的方式提醒我們,人的內心經歷過怎么樣的變故和猝不及防。
近鄉情怯:無法回歸的家鄉
中國的人口流動讓很多人變成了“流動人口”,而每一個在路上的人也許都有著自己無法言說的故事。家鄉,對于一些人來說,是失落的故園;對于另一些人而言,則是無法靠近的禁區。
1997年,王家衛的《春光乍泄》橫空出世,獲得當年國際影壇的矚目。他的電影,似乎都在講述一個母題,人的孤獨和回歸。《春光乍泄》看似講述人的情感,嵌入了多角戀和同性戀等元素,其實是標準的“奧德賽”的故事。主人公黎耀輝不知道在香港做了什么,讓他無法面對家人,獨自跑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以為在異鄉就可以重新開始,在經歷了各種遭遇后,他還是意識到自己應該回家。
如果說《奧德賽》是古典時代英雄史詩,《尤利斯西》是現代生活風俗畫,那《春光乍泄》可以看做是后現代都市的拼貼剪報。電影主人公那種“有生命力,但是生病了”(來自《攝氏零度》采訪)的狀態就是“97情結”下的都市病癥,一個人在精神和肉體放逐自我后的回歸之路。主人公流落在一個陌生的都市,他們從物理和心理時空上進一步拉大了與社會(香港)、家庭的距離,強化了他們本已濃厚滯重的無根感與漂泊感。
在鄧勇星的《到阜陽六百里》中,秦海璐飾演的女主角因個人問題不得不背井離鄉。天不遂人愿,在外多年的她沒有混出點名堂,不得不和老鄉擠在一間小房子里度日。為了多掙點錢,她和朋友想辦法弄了一輛違規車輛拉長途,想要騙回鄉心切的老鄉買車票。
在這部電影里,家鄉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歸的地方。女主人公在城市生活多年,無法適應回鄉,何況她不堪回首的過去也阻止她回家。最終,當她這個頗有些善意的“騙局”竟然成功,大家喜氣洋洋踏上回鄉之旅的時候,她卻退縮了……電影,就在這里戛然而止。
待不住的城市,回不了的鄉村,是當下中國外出工作的中青年普遍的困境。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面前,這個問題除了引發一些喟嘆似乎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回鄉又能如何?同樣是秦海璐作為主演的電影《榴蓮飄飄》,也是一個有家不想回的故事。主人公小燕利用旅游簽證在香港賣身掙錢,為的是回家舉辦一個風光的婚禮。熱鬧之后,最終還是以離婚收場,家鄉的戲校園也凋敝得不像樣子。兩部電影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后者甚至可以看做是前者的前傳。
范立欣的紀錄片《歸途列車》,直接表現了農民工這個群體的回家故事。鏡頭對準了民工這個春運的主力軍,表現了民工群體的艱辛和困境:張昌華和妻子陳素琴是四川的一對普通農民工夫婦,為了能讓家里過上更好的日子,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離開一對幼年的雙子女去廣州打工。他們辛苦賺錢往家里寄錢,幾年才能回去和家人團聚一次過一個年。但是,一對子女變成了“留守兒童”,他們和父母的感情生疏且淡漠。女兒甚至不聽勸阻,退學南下打工,復制父母的命運。
紀錄片由此記錄下暴力的一幕,張昌華對女兒的叛逆無可奈何,生氣打了她。而母親對此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依靠求神拜佛祈求女兒能夠懂事。兩代人的隔膜,因為春運的回家路被表現得更加集中。如果說,劇情片《過年》以戲劇性的場景表達了家庭觀念的異化,而《歸途列車》則直接以真實影像展現了農村的凋敝和家庭的實際上的徹底瓦解。

王家衛的《春光乍泄》劇照。
回家之旅:家庭價值的重構
以《人在囧途》為代表的“囧途系列”,則強調無論如何都要回家這個概念。徐崢和王寶強一個是老板,一個是民工,本來沒有交集,但因大雪引起的交通意外,讓這對不同背景的“難兄難弟”不得不一起踏上回家之路。徐崢本來是要回家和妻子離婚的,而王寶強的出現讓他打消了自己的念頭,重新理解了家庭的含義。
此后“囧途”系列一發不可收拾,成為春節檔的一個大“IP”:盡管故事發生的情境有所改變,但故事的開頭往往會設定一個家庭的危機,結尾處一定以合家歡,主角浪子回頭等情節作為結局。似乎不管外界的誘惑多么大,主人公的錯誤如何離譜,只要心中還有家庭的觀念,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紀錄片《四個春天》得以上映,受到不少觀眾的認可和喜愛。該片的導演陸慶屹少年離家,每年只有過年才回家和親人團聚,這本是最普通的中國人的生活,但難得他有心將自己每年回家的情形用家庭攝像機記錄下來,結合多年保存的家庭錄像帶,精心剪輯了一部紀錄片。電影以“四個春天”為切口,展現了父母極力營造的“田園牧歌”一般的生活,而家庭保存的錄像則打開了這個家庭近20年的變化以及他們不愿提及的傷感。

《四個春天》劇照。
坦率地說,這部作品在影像上并非上乘之作,所記錄的也不過是普通人的平凡小事。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贊譽,大抵因為這部紀錄片展現了中國人早已經失去卻一直向往的家庭模型和生活方式。陸慶屹的父母拉琴唱曲,幾個兄弟姊妹也一團和氣,20年間只有姐姐的去世讓這家人蒙上了陰影,但他們自足且自立,坦然面對生活。
有人認為這部作品不夠“真實”,生活里怎么會沒有矛盾呢?也有人認為,恰恰是這部作品展現的美好,反襯了大部分觀眾故鄉的失去和失落。電影中的父母親,難得在大時代里保留住了傳統家庭的凝聚力,他們四散的子女因此擁有了一個可以向往和歌詠的大家庭。我們為之感動,或許因為這種情感過于稀缺。
在中國人的文化里,家國往往是同構的,無數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也總是以此切題。如今想來,這場景似乎具有了更深的映射現實的意味。今年的春節,對于中國人來說,都是個人史上一個難忘的經歷;而對于一些無法回家的人來說,各種滋味恐怕體會得就更多。疫情過去,幸存的人們依然可以相聚,但犧牲和去世的人則無法再踏上回家的旅程。
于是,也不難聯想到王小帥電影《地久天長》的場景:失去了獨生子的夫婦斷絕了和所有朋友的聯系,除夕夜朋友送餃子來,他們禮貌地拒絕,偷偷收拾了行囊逃離了家鄉。他們之所以走,是因為每到歡聚的時候,就更要面對自己不愿意想起的傷痛。
編輯:袁冬雪
原標題:國產片中的人口流動和流動人口:個人、家庭、時代和國家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